王勇
大巴山是一條與秦嶺幾乎平行的山脈,但它的名氣沒有秦嶺那樣大。大巴山西接昆侖山,一直延伸到三峽神農(nóng)架,與長江對岸的湘西黔北的山脈相連,繞一圈就和青藏高原把四川盆地包裹在中間了。
大巴山南麓,嘉陵江、涪江與巴河、州河之間的一片地域,就是通常意義上的川北。由于地域原因,在天下分裂的時期,漢中成了秦嶺和大巴山、關(guān)中與西蜀之間的跳板,而跳板面前的川北就成了一片被反復(fù)爭奪的征戰(zhàn)之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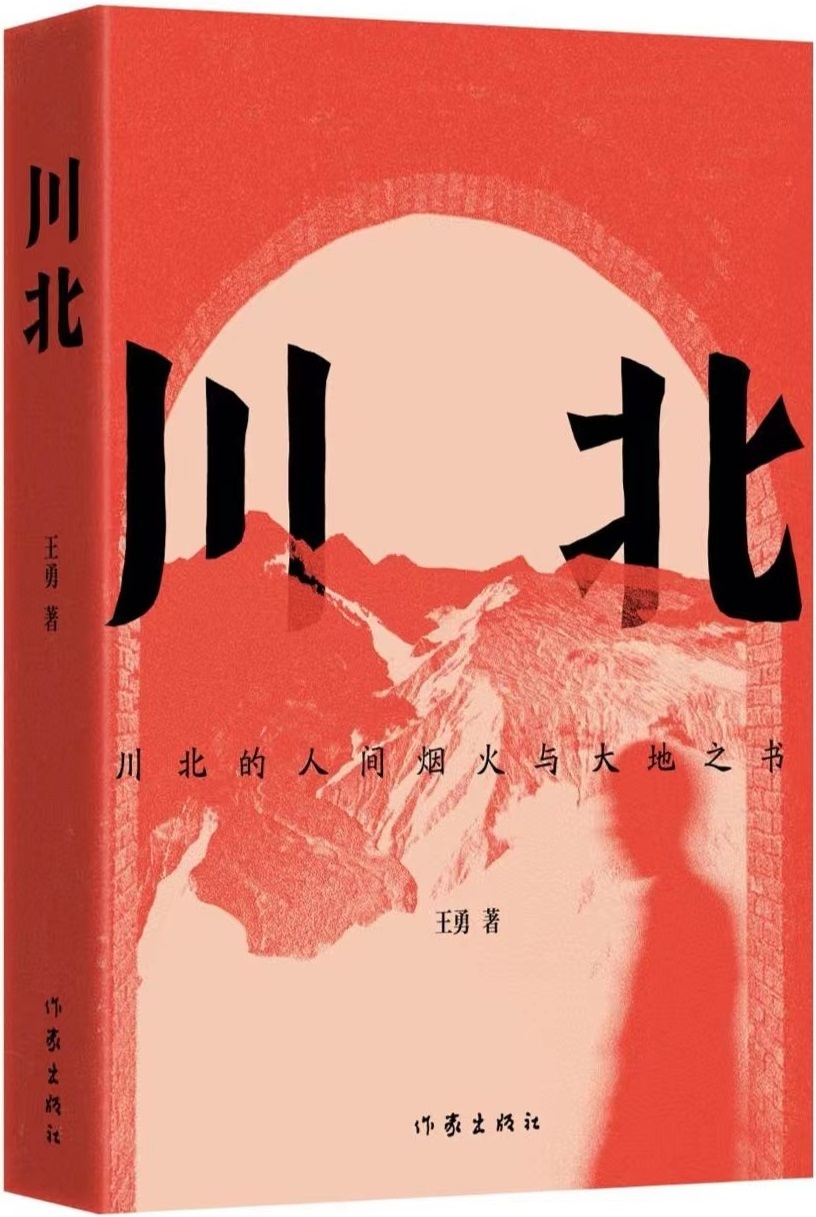
萌生寫一部關(guān)于川北的小說的想法,是在20世紀80年代,可謂多年前的一個夢想。我從小就生活在大巴山的鄉(xiāng)野,在那里讀書和勞作,在那里經(jīng)歷生活的磨難坎坷與少年的憂傷孤獨。幸運的是,我趕上了國家恢復(fù)高考,讀上了文學狂熱年代十二分紅火的中文專業(yè)。
我聽到過那片土地上無數(shù)口傳的生動故事與民歌,后來工作的全部時間也耗在了那片地域,大半個世紀我都沒有走出川北。自參加工作起,我盡力把少有的閑余時間用在了在川北土地上行走。因此我熟悉川北的每一個縣、每一個鄉(xiāng)鎮(zhèn),乃至很多村,見過三教九流的奇奇怪怪的人,收集和聽聞了無數(shù)的奇聞軼事。越是如此,越覺得非寫出一部書不可。
尤其是到了近年,知悉這片土地歷史的一代代人已經(jīng)衰老或故去。我不能讓這片土地上那些生動的過往,那些飽滿的激情與倔強的忍耐,無聲無息地湮滅于地下。我要讓土地說話,述說那連綿的苦難與不屈。
但是,一部長篇小說的寫作與跑一場馬拉松一樣,要的不僅是耐力,更要的是體力。工作原因,難得有大段時間靜心寫作,所以本書動筆的時間比較早,卻一直寫得不那么順暢,寫寫停停,停停寫寫。
直到近年,反而工作越繁重辛勞,寫作的思路越流暢。我利用所有業(yè)余時間寫作,消耗了數(shù)千張紙,數(shù)百支筆,總算完成了70多萬字的書稿,最后成型的這部書縮減到60多萬字。
無論作品寫得好壞,我堅持下來了。直到2023年秋分的晚上,敲完作品的最后一個字,我對著窗外的天空和青山長長地出了一口氣。無所謂喜悅,無所謂憂傷,就像德國作家托馬斯·曼說過的,終于完成了,它可能不好,但是完成了,只要能完成,它也就是好的。
但我的眼眶確實濕潤了,我為自己的堅持與頑強而感動,我終于制造出了一塊碩大粗笨的“磚頭”,完成了這樣一部告慰川北大地的書。幸運的是,書稿順利入選四川省作家協(xié)會2024年度重點作品扶持項目,更增加了我要盡快將此書呈現(xiàn)于讀者面前的自信。
車爾尼雪夫斯基說:“歷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,它完全是在田野中前進的,有時穿過塵埃,有時穿過泥濘,有時橫渡沼澤,有時行經(jīng)叢林。”為寫作本書,我閱讀了大量文史資料、族譜乃至民間野史、醫(yī)書、巫術(shù)、堪輿、碑文,進行了大量田間調(diào)查與走訪,力爭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,采用以點帶面、以小寫大的結(jié)構(gòu),通過川北大巴山下桃花灣一個家族半個多世紀的繁衍歷程,讓土地陳述川北的故事。
翻開川北所在的近代史,這里有農(nóng)耕社會的日常,有淳樸古雅的民風,有亂世里的愛情,也有為所欲為的草菅人命,更有時代迭變的波詭云譎。
仁義禮智,忠孝廉恥,壓抑與放縱,堅韌與掙扎,樸實與狡黠,傾軋與殺伐,苦難與良知,生養(yǎng)繁衍,愛恨情仇,一切都在時變境遷中洗澈沉浮,濾濁澄清。人間的苦痛、糾結(jié)與忍耐、欲望都飽含于這一片大地的泥土中。
由于讀書的駁雜,我的作品里既有中國古典文學和現(xiàn)代文學的影子,也有蘇俄批判現(xiàn)實主義、歐美現(xiàn)代派和后現(xiàn)代派的影子。我在熬制川北味道的麻辣火鍋,小說故事跨度50年,情節(jié)復(fù)雜,人物紛繁,現(xiàn)實與魔幻,牧歌與史詩,粗放與細膩,精雕細琢與濃墨重彩,大量風物、習俗、民歌有意識地加入,構(gòu)成五彩繽紛、眼花繚亂的畫卷。
那些生長故事的鄉(xiāng)土正在遠去,流逝的歲月只留下斑駁的遠影,消失的總有幾分懷念。后來人如能通過讀這部書知曉川北大地的過往與曾經(jīng),我亦感足矣。
(《川北》,王勇著,作家出版社,2025年9月)
【未經(jīng)授權(quán),嚴禁轉(zhuǎn)載!聯(lián)系電話028-86968276】















